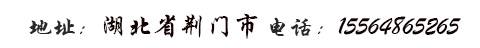庄子应帝王第七内篇
|
庄子《应帝王》(第七)内篇 原文 啮缺问于王倪,四问而四不知。啮缺因跃而大喜,行以告蒲衣子。 蒲衣子曰:“而乃今知之乎?有虞氏不及泰氏。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;亦得人矣,而未始出于非人。泰氏其卧徐徐,其觉于于。一以己为马,一以己为牛;其知情信,其德甚真,而未始入于非人。” 肩吾见狂接舆。狂接舆曰:“日中始何以语女?” 肩吾曰:“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,人孰敢不听而化诸!” 狂接舆曰:“是欺德也。其于治天下也。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。夫圣人之治也,治外乎?正而后行,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。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,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,而曾二虫之无知!” 天根游于殷阳,至蓼水之上,适遭无名人而问焉,曰:“请问为天下。” 无名人曰:“去!汝鄙人也,何问之不豫也!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,厌,则又乘夫莽眇之鸟,以出六极之外,而游无何有之乡,以处圹埌之野。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?” 又复问。 无名人曰:“汝游心于淡,合气于漠,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,而天下治矣。” 阳子居见老聃,曰:“有人于此,向疾强梁,物彻疏明,学道不勌。如是者,可比明王乎?” 老聃曰:“是于圣人也,胥易技系,劳形怵心者也。且也虎豹之文来田,猨狙之便执斄之狗来藉。如是者,可比明王乎?” 阳子居蹴然曰:“敢问明王之治。” 老聃曰:“明王之治: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,化贷万物而民弗恃;有莫举名,使物自喜;立乎不测,而游于无有者也。” 郑有神巫曰季咸,知人之死生存亡、祸福寿夭,期以岁月旬日,若神。郑人见之,皆弃而走。列子见之而心醉,归,以告壶子,曰:“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,则又有至焉者矣。” 壶子曰:“吾与汝既其文,未既其实,而固得道与?众雌而无雄,而又奚卵焉!而以道与世亢,必信,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尝试与来,以予示之。” 明日,列子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:”嘻!子之先生死矣!弗活矣!不以旬数矣!吾见怪焉,见湿灰焉。” 列子入,泣涕沾襟以告壶子。壶子曰:“乡吾示之以地文,萌乎不震不正。是殆见吾杜德机也。尝又与来。” 明日,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:“幸矣!子之先生遇我也,有瘳矣!全然有生矣!吾见其杜权矣!” 列子入,以告壶子。壶子曰:“乡吾示之以天壤,名实不入,而机发于踵。是殆见吾善者机也。尝又与来。” 明日,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:“子之先生不齐,吾无得而相焉。试齐,且复相之。” 列子入,以告壶子。壶子曰:“吾乡示之以太冲莫胜,是殆见吾衡气机也。鲩桓之审为渊,止水之审为渊,流水之审为渊。渊有九名,此处三焉。尝又与来。” 明日,又与之见壶子。立未定,自失而走。壶子曰:“追之!” 列子追之不及。反,以报壶曰:“已灭矣,已失矣,吾弗及已。” 壶子曰:“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与之虚而委蛇,不知其谁何,因以为弟靡,因以为波流,故逃也。” 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,三年不出。为其妻爨,食豕如食人。于事无与亲。雕琢复朴,块然独以其形立。纷而封哉,一以是终。 无为名尸,无为谋府;无为事任,无为知主。体尽无穷,而游无朕;尽其所受乎天,而无见得,亦虚而已!至人之用心若镜,不将不迎,应而不藏,故能胜物而不伤。 南海之帝为儵,北海之帝为忽,中央之帝为浑沌。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,浑沌待之甚善。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,曰:“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,此独无有,尝试凿之。”日凿一窍,七日而浑沌死。 译文 啮缺他问于王倪,一连相问了四次,王倪都不能作答。啮缺高兴跳起来,跑去告诉蒲衣子。 蒲衣子听了就说:你今天才知道吗?虞舜不如伏羲氏。虞舜他心怀仁义,以此来笼络人心;这样虽然也可以、得到百姓的拥戴,不过他还是不曾、摆脱俗务的牵累。伏羲氏在睡卧时,显得安闲而舒适,醒来悠游而自得;他不在乎人言论,任人称自己是马,任人称自己是牛;他的智慧能无伪,他的德行很纯真,他不受外物牵累。” 肩吾拜见狂接舆,狂接舆他问肩吾:“你的老师日中始,他教授你些什么?” 肩吾就对接舆说:“我的老师告诉我,做国君的一定要、凭借自己的意志,制定法规公布它,人民谁敢不听从,而去自行其是呢?” 接舆听了这样说:“日中始所教的是、自欺欺人的做法,这样去治理天下,那就好比是徒步、入海开凿出河道,同样好比让蚊虫、去背负大山一样。圣人治理天下时,难道是用法规去、治理社会表象吗?圣人是顺任本性,这样去施行感化,任人去各尽所能。鸟儿尚且能知道,要以高飞去躲避、罗网弓箭的伤害;鼹鼠尚且能知道、深藏神坛下洞穴,以避烟熏凿地祸。难道人竟然不如、这样两种小动物,以避法规的伤害?” 天根游殷山南面,来到蓼水河边上,正巧遇上无名人,便向无名人求教:“我愿向先生请教、治理天下的办法。” 无名人对天根说:“走开你这鄙陋人,为何一开口就问、让人扫兴的问题!我想去跟造物者、相识相融为一体,感到厌烦就乘着、状如飞鸟清虚气,飞出六极之外去,游于空虚无之乡,居于广阔无边地。你为什么拿所谓、治理天下的俗语,来扰乱我心情呢?” 天根又再次求问。 无名人就对他说:“你应保持心虚静,性情恬淡气平和,顺任自然无偏私,天下就可治理好。” 阳子居他持看法,拜见老聃对他说:“有这样的一个人,做事精明且果断,看事物有洞察力,了解透彻且通达,学道精勤不厌倦。这样的人可以和、圣哲之王相比吗?” 老聃听了对他说:“这样的人怎能跟、圣人相提并论呢?圣人看这样的人,不过像聪明小吏,办事为技能所累,劳苦身躯费心神。虎豹因皮毛花纹,招致众人来猎杀;猿猴因身体敏捷,狗因捕物很迅猛,招致绳索的拘缚。被才智所累的人,怎能跟圣王相比。” 阳子居听这番话,茫然惭愧地问说:“请问圣哲的君王,他是怎样治天下?” 老聃告诉阳子居:“圣哲之王治天下,他建功绩覆天下,像与自己不相干;他施教化普天下,然而百姓的心里、却不觉得依靠他;他虽然是有功德,却无方法来称誉;他使万事和万物、各得其所自欣悦。而他自己立足于、不可测度的境地,与虚无大道合一。” 郑国有一个巫师,他的名字叫季咸,看相十分的灵验。他是能算出人的、生死存亡的时限,祸福寿夭的状况,他所预先占卜的、年月旬日的时间,准确灵验真如神。郑国的人见了他,都因害怕忙跑开。列子见他而心醉,回来告诉壶子说:“我原认为先生的、道行是最高深的,见了季咸才知道,还有更为高深的。” 壶子听了这样说:“我所教授给你的,是道外在的东西,并不是道的实质;你就认为得道了?雌鸡若是无雄鸡,怎能生出受精卵?你凭学道的表面,去与世人相匹敌,想求得人的信任,这样一来会让人,洞察到你的心思。你把那个人请来,让他看看我的相。” 列子就于第二天,邀请季咸让他给、老师壶子看看相。季咸看完走出门,就对列子这样说:“唉你先生快死了!已经不能够活了,没有十天光景了!我看他形色怪异,面如遇水灰烬样。” 列子回到了屋里,泪水沾湿了衣服,把季咸话告先生。壶子听了这样说:“刚才我将沉静的、心相显露给他看,其相不动也不止,他看到我的闭塞,样子就像无生机。你请他来再看看。” 次日列子带季咸、来给壶子重看相,季咸看完走出门,就对列子这样说:“先生幸亏遇见我,现在已经有救了!完全有了生气了!我已观察到他的、闭塞生机活动了。” 列子回到了屋里,把季咸话告先生。壶子听了这样说:“刚才我给他看的,是天地间的生息;名声实利等杂念,都被排除于心外,生机从脚跟升起。他是只能够看到、我的这一线生机。你再请他来看看。” 列子就于第二天,邀请季咸来看相,季咸看完走出门,就对列子这样说:“先生精神显不足,并且神志还恍惚,我无法给他看相,等他心神安宁后,我再来给他看相。” 列子回到了屋里,把季咸话告先生。壶子听了这样说:“刚才我显给他看、无预兆的太虚境,他是只能看到我、气度持平的生机。鲸鱼盘旋的地方,那就能成为深渊;静止河水聚积处,那就能成为深渊;流动河水滞流处,那就能成为深渊;深渊有九种名称,以上是三种名称。季咸来给我看相,我就给他显示了、三种不同的生机。你再请他来看看。” 列子就于第二天,邀季咸来再看相。季咸进门未站稳,惊慌失色就跑了。壶子就对列子说:“你赶快去追回他!” 列子没追上季咸,回来告诉壶子说:“已经没有踪影了,不知他的去向了,我没能够追上他。” 壶子就对列子说:“刚才我显给他看、万象皆空的境域,并未显示我真相;境域闪烁不定的,犹如草望风而靡,犹如水随波逐流。他弄不清我究竟,所以只好逃跑了。” 列子这时才感到,没学老师的真经,回到自己的家里,三年都没有出门;真诚帮妻子做饭,喂猪就像侍候人;对世界上的事物,已经没有了偏私;抛弃浮华的修饰,复归质朴和纯真,木然忘情像大地,无知无识不染尘,在复杂的世界里、固守纯朴至终身。 不要去追求名利,不要热心用计谋,不要任事而专断,不要智巧的作为。领会无穷的大道,游心虚灵的境域,顺任自然的本性,无所表露不自得,达到空明的心境。修养极好的至人,用心如一面镜子,对来外物是即照,对去外物不会留。如实反映无隐藏,所以能反映外物。至人不损心费神。 南海帝王名叫儵,北海帝王名叫忽,中央帝王叫混沌。儵忽二帝常会于、中央大帝混沌处,混沌亲善待他们。儵忽要报答混沌,相互商量这样说:“人人都有眼和耳、以及口鼻七孔窍,用来看听吃呼吸;唯独混沌他没有。我们试着为混沌,凿出这七个孔窍。”他们就帮助混沌、一天开凿一孔窍,开凿到了第七天,混沌不幸死去了。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beihaigou.com/bhgfzfs/13486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慢游北海涠洲岛,浮生三日,吃穿住全攻略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