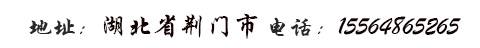风的声音
|
父亲走后,我将他埋在了新墓园。 今年与母亲一同前去,这是母亲的 次。这几日母亲把计划安排得满满当当:什么时候出发,买什么祭品,坐什么车等等。 ,我与她只乘上一辆私家车,一袋蜡烛和香。我提着一小盆花篮,只有菊花,黄灿灿的。车里闷得很,我稍稍摇下窗,闭上眼透起气,春天的风凉津津。“呼呼呼”,风吹起怀里的菊花,我似乎听见父亲的声音。我向外张望,只有呼啸而过的风景,还有一只奔跑的狗。 “嘿,你追得上我吗?”后视镜里的自己戏谑着追逐的狗。 母亲拍了拍我的左肩,我转过脸后立马耷拉了下来。我知道,在今日严肃的节日里不该如此张狂。我再看向她,修剪了一头比我还短的碎发,染的红棕发色与白银的发根格格不入,早已掉色的文眉,脸皮松垮。然而,她比我安静,腰板挺直,目视前方。按照我对她容易晕车的了解,试着化解一下尴尬的氛围,我说,妈,你不晕车吧?她摇了摇头。 这座墓园是新建的,几年中满山的石碑一块挨着一块矗立着。车子转弯,窗缝的风开始低吟,像是演奏一首首哀曲。我们下了车,听见炮区响彻的噼里啪啦,山野的林涛阵阵,还有远方细细的喵喵声。我们向前径直走去,穿过花圃、松树区和炮仗花生长的林荫小道。我停下了脚步,母亲问我怎么了。我说,到了。我看见父亲的石碑后有了斑驳,从行李掏出干布润点水轻轻擦拭,一遍又一遍。细耳谛听,石碑摩擦出的声响竟有点悦耳。将三支香点燃握在手中祈祷,我说,爸爸,我来了。一阵风吹过,后背生起冷汗。原来,父亲已然化作一阵风与我相见,无形却让我汗背。 是的,我坚信这阵风便是父亲,从未离去。他走的前一日正值寒冬,北海的北风狂烈。他问,你冷吗?我双手撺紧夹在大腿中。他扯起被角盖住我的双手,一股温热袭来。我听着窗外的风声,说,你冷吗?他笑了笑摇摇头。他丝毫不畏惧寒冷,用自己的余温温暖我的双手。今日我又伸出了双手抚摸起父亲的石碑,光滑且冰凉。我说,这一次,换我来暖你了。 说完,我看见离我们不远处生起一股旋风,卷起了尘埃。 我在父亲的墓前坐了下来,一起看我给他选择的墓园,视野开阔,依山傍水。阳光刺眼,我皱起眉头眺望起远方,一只鸟儿随着风势盘旋而上。风声似乎在说,你慢点飞,你慢点飞。 这句话有点耳熟,那是我高中时就听过的。父亲生前除了做电工,业余还养起猪。一辆陈旧的摩托车穿梭北海的大街小巷,车上的后座上永远残留黏腻的泔水。他总是很迟将我载去学校,车速飞快。我说,你慢点,慢点。他迎着风,说,你说什么,我听不清。我没有继续,而是将头埋在他的肩胛骨中,一路向西。泔水的味道永远呛人,临近学校我拍起他的后背“啪啪啪”,示意停车。他知道我的心思,目送我。我走着,跑着,还远远地听见他的“不急,你慢点跑!” 祭祀很快,我坐在走廊看起逐渐高升的太阳。也是这样的阳光,父亲走的那天忽然转晴。我走出病房,抬头看起又远又近的太阳,伸出五指又张又合。一片树叶随风飘了下来,我抓住,凑鼻嗅了嗅,清新萦绕了好久。我再看起大树留下在路上的参差阳光,犹如脚印。我想,那是父亲随风去了,踩着一路的阳光。 “赞峰,回去了。”母亲此时唤起我。 我拍了拍臀部,摘下一朵炮仗花,金橙如血,大口张开。我捧着这朵鲜艳的炮仗花回到墓位,敬重地给父亲献上。清风徐来,我嗅到别样的味道。 车辆驶出墓园,又开始了颠簸。没过多久,我见到了来时的那只狗,安静地趴在原处,眼睛巴巴地看着我。它似乎在等我,我摇下窗掰下一块蛋糕向它掷去,它又追起我。我突然发现,我们这一生都在与风比赛,追着前人的身影。 窗外的风声呼啸,我大声喊着:“你慢点跑!” 梅李子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beihaigou.com/bhgwxtz/726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比特犬价格纯种比特幼犬多少钱一只
- 下一篇文章: 沙雕可爱